吴大观采访札记:信仰的力量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摘自电视剧《潜伏》片尾曲《深海》

青年求学时期和参加工作后的吴大观。
新华网北京6月30日电(俞玮)信仰,可以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力量?在采访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的先进事迹前,我在网上搜寻了一下关于他的报道,得到了这样一些信息:
——191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中学毕业于百年名校扬州中学,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并赴美留学,是一个接受过良好中西方教育的典型知识分子;
——求学期间,因眼见日寇飞机轰炸神州、无数国人惨死,而毅然由机械系改报航空系,从此一生执着于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制;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起连续46年每月“多交党费”累计21万元左右,给希望工程等各项捐款9万元,临终前除了给老伴留下一些生活费外,剩余10万元积蓄全部上交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尽管在“文革”时遭受磨难左眼完全失明,却丝毫没有动摇他“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生命最后30年就用一只右眼如饥似渴地工作着;
——得知身患癌症后,非但没有想办法延长生命,反而因时日无多更加抓紧时间看报学习,最后一个月住院期间,拒绝让医生给他用昂贵的进口药,表示“没必要为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而浪费国家的钱”,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都会起身挣扎着把针头拔掉……
有人说,看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做出的选择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那么,吴大观呢?跟随中宣部中央采访团的8天采访,从沈阳到西安,再回到北京,沿着他的人生轨迹我试图走进那段历史岁月,也在潜意识里寻找着一个答案……
在沈阳,我第一次与那么多老人、那么多老一辈的航空人近距离接触,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诉说往事时洋溢出的激情。也许,在他们心里,他们不是在谈吴大观,而是在讲述航空人这个群体。在当年既缺国家长远规划,又缺资金的情况下,明知发动机研制周期长达20多年且不容易出成绩,但是为了“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们甘愿走在这条寂寞而艰难的道路上,无怨无悔。

6月14日,新华网记者采访吴大观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共事时的同事王振华。新华网图片
在西安,当我采访王振华老人时,泪水更是模糊了视线。王振华是湖南长沙人,和吴大观在西安航空发动机研究所曾共事过几年。他告诉我,当年日军轰炸他家的村庄,村民们无处藏身,只好躲到洞庭湖的船上去。但是后来还是被发现了,日本人就在湖上进行疯狂扫射,只有10岁的他和爷爷等少数几人幸免遇难。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掀开被角看到日本飞机在头上飞过,一边一个红太阳,飞行员的模样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说,鲜血把湖水染成了红色,那一刻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学航空,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保卫我们的国家。从湖南雅礼中学(当年耶鲁大学在长沙办的学校)毕业后,老人做出了和吴大观一样的选择——报航空系。
在吴大观的口述自传里,有这样一段话:那时西南联大有一半教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奋斗事业中。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这些穷学生一样,衣着俭朴、清贫如洗,但他们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王振华老人已经退休了,他的退休工资是1700元。当我把这个数字告诉其他同行的记者时,他们都忍不住吃惊地说“不会吧?”大家不敢置信,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无私奉献了一辈子的这些老同志,却只有这么一点退休工资?但是,我清楚地记得,老人后来说:“只要我们装备了我们的空军,就行了。”
第二天,乘飞机从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我一直在看吴大观的口述自传《我的“中国心”》。他提到自己早年曾经在国民党建的旧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工作,那是在贵州大定(现在的贵州省大方县)。尽管很穷,还是个“土匪窝”,但是大家抱着满腔的爱国之情,并没有退缩。然而,“在国民党那个年代,国运凋敝、民不聊生,根本是不可能聚精会神地把我国航空工业搞上去的。”看清之后,吴大观便和爱人一起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里。
之后他们去了北大工学院任教,并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到了解放区。吴大观在书中写道:“1948年,在解放区,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联想起,在从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的途中,在广州逗留的日子里,我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去电影院看了一次电影……影片的名字叫《悲惨世界》,我一连看了两遍……电影里有一句话是‘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我记了一辈子,而且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这一句话……”

吴大观的入党介绍人沈时荃老人。新华网 俞玮 摄
这,就是他那时的信仰吧,坚信唯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后来,他见到了聂荣臻元帅和一批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他们的作风跟国民党和美国军人的完全不同。“他们就是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要跟着共产党,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美好的未来,也更加明确了一生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1949年11月,吴大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采访他的入党介绍人沈时荃老人时,老人因年事已高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反复地说:“我这辈子介绍入党的人不多,在我介绍的人中,他算得上是个模范。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党组织却从来不提要求。现在像他这样的人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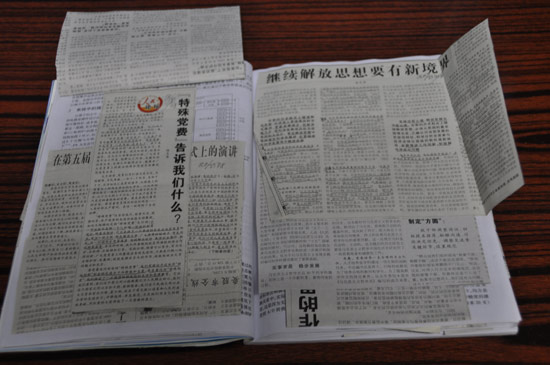
吴老喜欢读报、剪报
新华网北京6月30日电(俞玮)吴大观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他认为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并坚持做学习笔记。随意翻开其中一本,看到他在2008年7月13日学习完《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后写道:人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对社会主义增加一天的认识,增加一天的信仰,心情增加一天的舒畅。正是因为热爱学习,勤于思考,他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修养,从而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文革”时期,吴大观挨批斗、被鞭子抽,左眼完全失明,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说:“这是少数人犯的错误,不是我们党的错。”恢复工作后,他就用一只视力仅剩0.3的右眼如饥似渴地继续为“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奋斗着,直至生命的终点。
吴大观认为,“文革”是中国的灾难,但是它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太无知、太没有经验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后人又没有走成功的一条路。我们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认识,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总结前面经验作出的决策。”
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中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吴大观不是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接触过“花花世界”,但是他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选择了“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并为之奋斗终身,坚定而忠诚。
正如他在2009年1月19日学习完《人民日报》文章《开辟前进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的笔记页端写道: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吴大观的女儿可能遗传了父亲性格里比较“直”的一面,为人非常爽直。回到北京第一天,大家让她介绍一下自己的父亲吴大观,她说:“我爸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但是,她却说出了一件在我看来极为不普通的事。

图为吴大观家客厅里既当餐桌又当书桌的一张折叠桌子,老人就是在这张桌上学习和吃饭。新华网 俞玮 摄
2004年,吴大观88岁,他的身体实在是不允许他再去单位上班了。没办法,他就在家给自己制定了工作学习表。他家客厅有一张餐桌,就是80年代那种很多人家里都有的木折叠桌子。每天早上7点,他在这张卓上学习,中午在这张桌上吃饭,下午继续学,边学边做笔记……
两会期间,吴大观就更加认真,还组织老伴讨论。吴晓云问他:“您都退休了,还组织我妈学习什么呀?”他回答说:“我们也要认真学习,认真领会党的精神,到时候自己要做好。”不仅如此,他还会和老伴互相督促着把一些重要精神背下来,彼此再检查对方背得是否正确,有没有落字……
或许,这就是有信仰与没信仰的区别。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有追求的人,时刻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持着他往前走。即使身体离岗,但精神永远不会离岗。
在吴大观的一生中,做得最持久的两件大事,除了68年与航空相依相伴之外,还有一件就是他连续46年多交党费。许多记者私下谈论时都流露出了不理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942年4月15日,吴大观夫妇摄于昆明。
在他的自传里,有一章叫《感悟人生》,其中有三段话谈到了这件事。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应该感谢党,我应该对党多做一点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名之下,难副其实,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内心挺舒服、挺高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最近报纸还有报道,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是这个想法。”
“也有人说我是傻瓜,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这么过来的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点不过分。我从1964年开始多交党费,中间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终我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话落无声却有力。这位朴实的老人用93年的人生实现了自己“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实现了60年前在党旗下举起右手说出的那句铮铮誓言。(摘编自新华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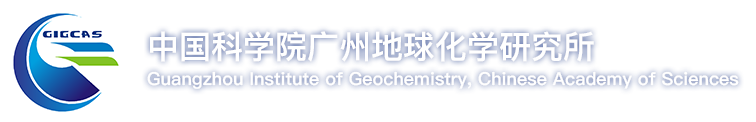
 党群园地
党群园地
